鼓掌——古代世界“大数据”
公元七世纪,东罗马帝国正处在它“衰亡史”的衰落时期,当时的皇帝厄拉克利斯(Heraclius)计划会见一位蛮族君王。厄拉克利斯想威慑他的敌人,但他知道每况愈下的罗马军队已雄风不再,尤其当敌人是蛮族时,完全不能起到威慑的作用。于是他雇用了一批人来壮大他的军队——其目的就是造势。
厄拉克利斯的虚张声势战术,也可以说是波将金村的有声版本。它并没有能够挽救一个不断衰亡的帝国,但这件事却给从罗马帝国和人类历史上最早最普遍的互动方式——鼓掌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恰当的注释。在古代,鼓掌是赞扬,同时也是沟通,它成为了一种力量。弱小的人类通过双手发出的“雷鸣”,重塑了自然界中的隆隆作响和噼里啪啦。
今天的鼓掌与那时大致相同。在片场、剧院以及任何人们身份变成观众地方,我们都会拍合手掌来表示赞赏。简言之,我们找到了作为群体来表达自己的方式——正是通过我们群体式的方法。
但同时我们也不断在“无手”世界里对鼓掌进行革新。我们会称赞彼此在Facebook上的新鲜事,相互分享和联系,我们转发微博上的好东西来扩大它的影响力。我们添加好友、关注某人的微博、点一下“+1”(Google+上的推荐网站功能)、点一下“推荐”、“@”一下、发布“友情链接”等等,我们认识到在网络时代中这样一个更大的观众群体成为了为自己鼓掌的人。
下面的故事说的是大多数情况下当人们可以用的只有双手时,他们是怎样表示赞扬的——在我们不懂什么是喜欢之前是怎样表达喜欢的。鼓掌行为是大众传媒的一种早期形式,因为展示的同时又有参与,也因为它即时、可视,当然也可闻,鼓掌将人们彼此、人们与[*{b}*]联系起来。它是对公众情绪的分析,透露出彼此联系的人们的倾向和愿望。它是特定的自我为以数量取胜的群体让路。它是在那个没有“大数据”年代的大数据。
“它是调查民意的方法”
学者们对鼓掌的起源并不确定。他们所了解的鼓掌是古老的、普遍的,也是经久不衰的——“人类文化若比作宝石,鼓掌就是它显着而稳定的一个刻面”。它似乎是婴儿的本能行为。《圣经》里也多次提到鼓掌——为了赞赏,也为了庆祝,“他们拥他为王,以涂油礼给他加冕,并拍手称颂:‘吾王万岁!’”
但鼓掌是在剧院里——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变得正式起来。“鼓掌(plaudits)”源自拉丁语,意为“击打”、“爆发”,是一场戏落幕的常见方式。谢幕时,主角会喊一声“Valete et plaudite!”(“再见!鼓掌吧!”)从而示意观众鼓掌。几个世纪以来戏剧演员用他们所偏爱的这种微妙的方式告诉观众:该对演出给予赞扬了。显然,他也因此把自身变成了人类*9次鼓掌的标志之一。
由于戏剧和政治的融合——尤其是在罗马帝国取代罗马共和国之后——鼓掌成为了统治者与民众直接(当然在意识心态上是完全间接地)互动的方式。政治人物用来衡量他们在民众心中地位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衡量他们在走进竞技场时受到的欢迎程度。统治者们都变成了灵敏的人体掌声测量仪,读出音量、速度、节奏和时长——作为他们预测政治前途的依据。
在威斯康辛大学从事历史和人文研究,也是《古罗马手势与喝彩》一书作者的格雷格?阿尔德雷特(Greg Aldrete)教授说:“你几乎可以把它看作古代民意测验。这是你评判人民态度,调查人民情感倾向的方式。”
在那没有电话不能进行盖洛普式民调的时代,古罗马的统治者们就在听掌声的过程中收集着有关民众的数据。他们把得到的数据结果与在场演出的表演者得到的掌声进行比较。如果一个演员得到的掌声比给他的还要热烈,卡里古拉大帝(Caligula,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会说:“我真希望所有罗马人只有一个脖子。”
瓦式、砖式、蜂式
随着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和世袭制度,鼓掌变得愈发微妙和系统化。鼓掌不再仅仅意味着“拍手”。尽管古希腊罗马的人们肯定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拍击手掌,但他们的鼓掌与单纯的拍手大不相同。掌声有时如震耳雷鸣,有时也像嗡嗡蜂音,有时则更像颤抖。观众们发展出各种方式来表达不同程度的赞同,全手相碰的鼓掌、只动手指的鼓掌、牵动衣袖的挥手。其中,最后一种手势后来被奥利列安大帝以挥舞手绢取代。这是他贡献给罗马公民的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他们再也不会无法表达对他的赞美。
在帝国的扩张中,鼓掌礼也受到了异族文化的影响。就尼禄而言,埃及人制造大的声响以表达赞扬的方法令他印象深刻。
亚历山大式的“分贝制造”在当时主要有三类:砖式、瓦式、蜂式。前两种似乎对应的就是今天的鼓掌——“砖式”形容手如板砖般平直地鼓掌,“瓦式”形容手掌弯起来的鼓掌(参照古罗马建筑常见的弯曲的瓦片)。第三种则更多是声音上的表现而非动作上——起哄的人群发出巨大的蜂群一般的声音。
罗马竞技场的“有问必答”
鼓掌成为了一门政治的技艺,一个统治者和公民共用的交流方式。当然,对罗马而言,它绝不是特效药。或者说,对整个古代世界都不是。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描写了一场有斯大林出席的地区党委会议。与会人员向这位[*{b}*]致意,鼓掌长达十分钟。斯大林的声名是如此卓越,谁都不愿成为*9个停下拍手的人。最后,一个造纸厂的主管*8坐下,众人便也都跟着落座。而会议结束后,这位主管就被逮捕了。
但在这位独裁者自己看来,苏联式的独裁是难以维持的——在罗马这样一个广阔的帝国尤是如此。帝国的统治者们如此有计划地在他们征服的土地上修建露天剧场和赛马场的原因之一就是:给他们的景观贴上罗马的标签,植入关于罗马的归属感。不过,另一方面,也是提供一个让分散的人们聚集为“等待发号施令的人群”的场所。
露天剧场是政权交接的地方。“成为一个合法的君主,”阿尔德雷特说,“你需要当众接受人们的鼓掌祝贺。”因此,剧场是罗马对广播和电视的原始回应,是古典版的Twitter问答、YouTube空间和Reddit有问必答:他们带来了政治自由的幻象。而同时作为媒介和信息的鼓掌,成为了表演的传达工具。通过它,人们对他们的[*{b}*]给出回应:以蜂群般的呼声和雷鸣般的掌声。
这壮观景象,反过来又合法化并增强了罗马的权力。“当你发现人群反复吟诵‘向恺撒致敬’时,”阿尔德雷特写道,“便塑造了一个恺撒”。
“看,我就说这好玩儿吧”
毫无疑问,那时起,权贵便开始了操控群众的事业。与其说群众,倒不如说愚民来得更贴切,向来易被操纵。阿尔德雷特告诉我,罗马和它的剧院,见证了“职业政治煽动者”这一群体的兴起:laudiceni(为他们的晚餐而鼓掌的人)被雇来混在人群中,煽动人们对政治表演的反应。最早这么干的大概是演员们:雇12个左右的“托儿”,分散在观众中延长鼓掌的时间——如果这令人感到无耻或可憎的话,“托儿”们就在人群中进行“自发的、无意识的”喝彩。
后来,这种方法开始被用在法庭上。律师们可能会雇用职业的“乌合之众的唤醒人”对法庭辩论做出强烈的表态,借此影响摇摆不定的法官。最后,它也成了政界的手段。
传闻中,尼禄征募了5000士兵在他讲演的时候喝彩。几个世纪后,米尔顿?伯利江郎才欲尽之时,也让大笑音轨的发明者查理?道格拉斯在他的表演中事先插入几段狂笑的声音。道格拉斯当然很容易满足他的要求。“看,我就说这儿好笑吧!”伯利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罗马人做的也是相同的编排。只是,他们是要用实时的操控气氛来满足自己。
又过了几个世纪,法国演员的“捧场团”使得这一机制更约定俗成。十六世纪有个法国诗人叫让?多拉,他所获得的赞誉和指责,大都来自他的“复古”:他买了一大堆自己写的戏的票,分发给那些承诺会在演出结束时鼓掌的人。19世纪20年代初期前,“捧场团”就已经制度化下来:巴黎的一位演出代理商详细地说明了“托儿”服务的重要性,潜规则于是成为显规则。
在《城市政权与法国城市的崛起》一书中,历史学家威廉.B.科恩描述了一则呈现给目标客户的复杂的“托儿”服务价目表:礼貌轻拍需要这么这么多钱,热烈鼓掌需要那么那么多钱,不留情面去砸别人场子又是一个数。
“捧场团”内部的分工也逐渐细化:rieurs-专门负责在喜剧节目大笑;pleureurs-职业装哭;commissaries-用心挖掘喜剧或乐曲最精妙的部分,然后去引起大家的关注;chatouilleurs-使观众保持微醺一般的好心情-;bisseurs-安可(返场)专业户。显然,*9个是最讨喜的。
缓慢而有节奏地鼓掌
鼓掌这一行为自身也在逐渐进化。音乐厅和戏院越发成为严肃的场合,并与宗教仪式的敬畏与崇高联系在了一起。随后,录音技术诞生,戏剧表演进入机械复制时代,它们也进一步安静了下来。知道何时该安静,何时该鼓掌,成为了教养的标志之一,也是观众们需要学习的新密码。鼓掌成为了关乎“做”与“不做”、“全部”与“无”、“安静沉着”与“洋洋得意”的礼节,先前的隐晦意义与微妙性都不复存在。
这些变化自然也改变了演员们。鼓掌不再是与观众的一次对话,而更像是演员与观众间某种野蛮的交易。它是承诺,又是取笑。于是后世中,罗马竞技场里鼓掌与它们丰富的含义,终于让步于被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鼓掌行为。不过这样一来,情况也变得有些混乱。不同的笑声混合在一起时,制造了一种呆板的放纵。鼓掌不再是一种奖励,而是理所应当的仪式。鼓掌在艺术家们眼中变得生硬。见多了崇拜与赞美的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就曾抱怨说:“人们鼓掌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该付他们钱吗?对他们道谢吗?拎起裙角致意吗?”
不合常理的,反而成为了一种沟通,史翠珊就表示她知道该如何回应没有掌声的状况。
而现在,我们又在呼唤那“微妙性”的回归。我们企图以新的方法改造鼓掌,使它恢复曾经的模样,做回那个意蕴丰富的集体的沟通方式。我们发明了一种缓慢而有节奏的鼓掌——语言学家约翰?海曼在他的书《说空话不费力:讽刺、疏远和语言的演化》中将它负责又欣喜地描述为“一个沉重单调、囿于重复的鼓掌手势”。
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用信息时代的便利资源重做公开的赞美。我们互动、点赞、分享,我们以鼠标和按键制造的那一大波“喜欢”,成为席卷互联网世界的浪潮。在互联网这个大戏院里,我们仅仅通过参与,便也成为了出场的一员。我们自身的参与使这戏的规模愈发壮大,而这恰是我们表达欣赏、认同的方式。我们清楚,这个崭新的世界给予自己的新角色。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我们的鼓掌就是这“整体景观”的一部分。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捧场者”。
而现在,在许多层面上,我们的鼓掌更有意义了,因为它们不再是昙花一现的事物。它们自身就是表演,它们包含的赞扬得以保持,它们的韵律被写在磁道上,它们的方式被分析和开发。它们传达出远多于拍手动作本身的信息。我们发出的喝彩鸦雀无声,却又如雷贯耳。-
热门资讯
-
IPO财务核查效力有多大 堰塞湖仍有压力 高顿教育 2023-06-07 10:0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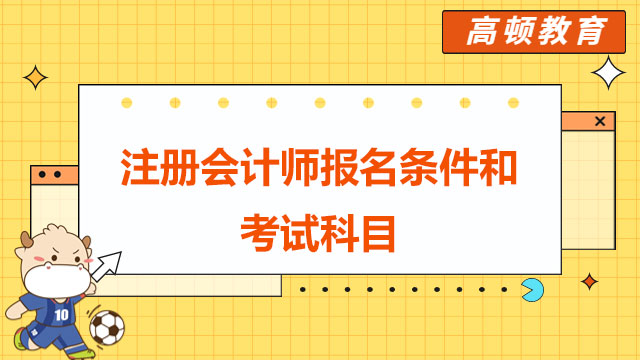
-
CPA考试可以自学吗?怎么学? 高顿教育 2022-05-29 09:06:25

-
2022年的税务师教材什么时候可以购买 高顿教育 2022-01-26 09:24:41
-
大数据应用促税务稽查提质增效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7:03
-
国家税务局: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超万亿元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4:50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