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我们见证了加息预期而非加息本身对这个系统形成的共振,冲击波沿着“资本密集型货币(美、欧、日)——劳动密集型货币(中、印)——资源密集型货币(俄、巴、澳)”这一货币链冲击并不断加重,新兴国家尤其是那些外汇储备欠缺且外部融资能力差的国家,正处在货币危机的边缘(巴西和俄罗斯刚被下调评级),而发达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本身,似乎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独善其身。
数据显示,最近几个月美国的股市下跌也是历史罕见,资本流失也较为严重。这似乎正在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全球化“风险污染”难题(类似环境污染问题):资源密集型国家资产不用多说,前所未有的大宗商品熊市已经让这些国家的生产函数处于盈亏平衡点的刀刃上(石油、铁矿石、黄金等均已经接近或跌破成本)。
劳动密集型国家中,中国由于过去人口红利在投资支出上的过度透支,形成的过剩产能仍然无法有效出清,但本意在保持内外部平衡的股票池和外汇池则面临“干涸”的危险,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导致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优势快速衰减。
印度虽然出现人口红利,但支撑规模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动员机制仍然不足;日本量化宽松虎头蛇尾,徘徊在0左右的通胀率已经显示摆脱紧缩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欧元区虽然暂时稳定,但希腊们的隐患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及财政和货币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解,如今法国经济又显疲态,德国经济仍是中流砥柱,但欧元区宽松形成的泡沫隐患也在内部集聚(德意志银行在次贷危机后收集和持有的天量衍生品头寸广受诟病)。
美国作为世界基础货币的输出国,虽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铸币税并输出通胀,但却很难完全输出泡沫,华尔街享受着这一场由量化宽松和零利率带来的免费盛宴,将传统的资本资产套利模型用到了极致,用货币市场的廉价资金跨期、跨市、跨国套利,同时将美国自身的风险资产泡沫一次又一次推上历史新高。所以我们面临的窘境是,当一场暴风雨已经来临,但纵览全球竟无稳定、称职的避险资产。
这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景观并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参考。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竟然发现当前全球的金融资产交易,正面临着与四十年前全球贸易领域“特里芬难题”相类似的难题,那就是——不断膨胀的金融资产泡沫与有限的美元货币供给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
全球天量的金融资产及衍生品交易、场内资产及场外影子资产的交易,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的以美元进行定价结算,但美元虽然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硬约束,但是仍然受到美国国家信用的软约束(这一软约束的硬性体现就是通货膨涨,这上升到美国政治层面),因此美元的供给是不可能无限大的。
四十年前,全球贸易额的快速扩大与黄金挂钩下的美元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如今,新的难题来了:全球金融资产泡沫的快速扩大与国家信用约束下的美元供给不足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后果正在显现,那就是全球金融资产泡沫与美元的紧缩预期之间的冲突,而前者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旧的特里芬难题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那么美元的“新特里芬难题”将导致全球货币体系转向何方?回归实用主义,这种类比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美国通胀没有达到目标通胀率之前,我们可能看到美元政策对金融风险的又一轮屈服,而这对我们的大类资产配置至关重要。
本文来源:新浪专栏
本文来源:新浪专栏
热门资讯
-
IPO财务核查效力有多大 堰塞湖仍有压力 高顿教育 2023-06-07 10:0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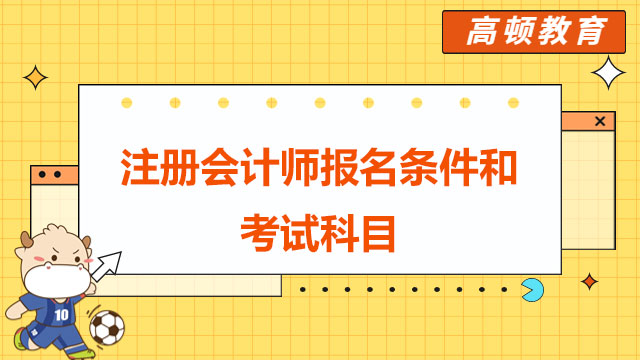
-
CPA考试可以自学吗?怎么学? 高顿教育 2022-05-29 09:06:25

-
2022年的税务师教材什么时候可以购买 高顿教育 2022-01-26 09:24:41
-
大数据应用促税务稽查提质增效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7:03
-
国家税务局: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超万亿元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4:50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