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听来似乎没有多大差别。“合作”是农民把各自的土地、耕牛和农具等放到一起共同使用。“集体”呢?就是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概归集体公有,再由集体成员共同使用。从私产共用到公产共用,反正都区别于私产私用的小农经济,不过公有程度有点不同,合作算初级,集体算高级,至于全民所有那就更高级——这就是当年的流行认识。
事后看,大错特错。关键是,一旦搞成了集体,权利主体的边界就起了模糊。主要是,集体成员不再限于入社社员,即使当年没把土地、耕牛和其他生产工具入社的非社员,也可以是集体成员,也享有与入社社员同等的权利。这里的非入社社员,可以是嫁给入社社员的外地农民;可以是入社社员在入社后新生的子女;还可以是合乎政策迁入本地的农民或非农民。总之,在“集体”架构下,入社社员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将与非入社社员一起拥有。
没有研究湄潭经验之前,我自己对公社体制的认识,实在还很肤浅。讲起来年头也不算短:下乡10年,虽在军队管理的国有农场劳动,但因为分配到山上狩猎,与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靠得比较近,耳闻目睹,对集体大锅饭有点感性认识。后来回城上大学,机缘巧合到杜老(杜润生)门下工作,参加农村调查的次数不少。可是对公社体制,看到了一些浅病灶,却不知晓还有深病灶——农民之间的权利边界不清,不断地互相吃大锅饭。
湄潭首创“增人不增地”,把我对公社的认知推进了一步。集体制区别于合作制的,可不仅仅只是组织规模过大,缺乏有效激励而发生“监管者偷懒”,进而难以衡量社员对集体劳动的个人贡献,结果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大伙儿只好吃开了大锅饭。这套体制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天生就有权充当集体成员——即便他们从来没有带着土地和其他财产入社。这可是一个敞开口子的集体制大锅饭!
那时把从湄潭得来的调查资料,带回北京反复研读。边读边想,我问过自己一个问题:这么一套成员身份开放的制度,究竟从哪里来的?应该与中国传统无缘,因为我们的农耕文明,基础是家庭私产——农民的家庭内部有个小锅饭,同财共居,添丁增劳一起劳作、一起生活;儿子成家后要分家,分的也是家庭的土地。出了家庭之门,土地、财产、人口的边界泾渭分明,没有张家增人,就去分李家土地这回事。
家庭私产也是私有制,搞社会主义当然要触及。不过经典理论的设想,丧钟将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首先敲响。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应该早就粉碎了小私有制,把小私有者分化为无产者与资产者,所以到了闹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农民作为小私产者早就作古了才对。布尔什维克成功之初搞“战时共产主义”,环境是一方面,主观上恐怕也是以为打烂了小私有者的坛坛罐罐,才更方便搞社会主义。
教训是吃不上饭。列宁转得快,提出“新经济政策”。农村方面,就是还要承认农民私产的一席之地。至于将来怎么办?列宁临去世前口授过一篇“论合作制”,大意是将来也不能剥夺农民这样的小私产者,只能引导他们走合作之路。这里的合作制,其实是农民私产基础上的一份自愿合约——土地、耕畜、农具之类按约入社,计价论权,共同使用,收益分红。入社社员的身份边界是明确的,这一点与入股股民相似,只有拿了财产“入”公司的,才有股民资格和相应权益。谁也不能当没入过股的股民,更不能说谁家添丁增人,就可以把其他股民的股权稀释一把的。
列宁去世不久,新经济政策连同合作社一起寿终正寝。斯大林要另搞一套。农村方面,他的纲领是“全盘集体化”,主要政策是把已全部国有化的土地永久地交给集体农庄(最早叫“劳动组合”)使用;国家凭工业垄断的优势在农村遍设国有拖拉机站,以机耕服务交换集体农民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0.00% 资金 研报];此种交换绝不等价,服从着名的“剪刀差”准则(国家工业品定价高,农产品定价低);农民的耕畜、农具全部归集体,集体划出部分资源归农户“自留”,其余则靠集体劳动、领取集体分配的报酬。
斯大林不但要消灭农村私有制,而且“要从肉体上消灭富农”——以及其他反对全盘集体化的农民。结果是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然后就是天怒人怨的大饥荒。政策也被迫作出过局部调整,无非是坚持集体化的前提下,略为增加农民的自留经济。但是直到斯大林去世,苏联粮食产量始终没有超过沙皇时代。
不过后来批判斯大林的,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神化”这位苏联领导人。我的看法,斯大林再厉害,实际上也做不到仅凭一己之见,就把苏联偌大的农村全盘推入集体化。[*{b}*]意志、意识形态和国家强力固然有超强的影响力,但涉及底层老百姓的经济组织方式,却不能完全归于斯大林个人的“能耐”。
长期来看,千百万人来自传统的习俗,对任何经济组织与制度的形成,起着非常基础的作用。就我的阅读所知,苏联农村集体经济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息息相关。这个传统,就是俄国的“村社”。我们或许可以说,至少斯大林是借助了俄国的村社传统,才做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全盘集体化。“俄国村社(Russian Mir)”说来话长。不过长话也可以短说,这套起自沙俄的农奴组织,基本支撑条件是俄罗斯特有的地广人稀。那里辽阔的俄罗斯土地统归沙皇,但皇家也管不过来,于是永久地把土地交给村社使用,村社则行份地制——每个村社的成员都有权领取一份土地耕作,对应的义务则是缴纳税赋。村社土地“定期重分”,以适应成员家庭人口变动的要求——增人增地、减人减地,满足村社成员平均利用土地的诉求。既然村社如此慷慨,俄罗斯农民哪里舍得独立在外?这里不是独立农民基于土地私产的自由契约,而是对村社和沙皇一体化的人身依附。有一首沙俄民歌这样唱,“哪里有村社的手,哪里就是我的头”!
事实上,即使在1905-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以后,俄国也只有小部分农民完全摆脱了农奴状态,成为西欧意义上的“小农”。这样看,列宁的合作制虽然校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偏颇,但也难接俄罗斯传统的地气。相比之下,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却容易接轨传统:国家把国有化土地交集体农庄使用,以换取工业化所需的粮食,以及国家资本积累。苏联农民也依附于集体——例如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根本没有公民自由迁徙权这一说,苏联农民进城要查验“身份护照”,那是我们在本系列之(12)“老大哥的坏榜样”里介绍过的。
从村社到全盘集体化,对苏俄的农业、国民经济、乃至国家体制究竟有什么影响,感兴趣的读者怕要请教行家。这里要讲的是,无论“村社-集体制”对苏联的作用如何,中国却断然没有村社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向来以农民家庭私产为基础,家内有点小锅饭,家庭之间权利边界分明。这是中华农耕文明早就发达的一个基础。农业早发达,人丁兴旺,可养育的人口总规模也大,反过来以不断增长的人口无限细分耕地,这么一条发展道路就越走越窄。
给定中国之国情,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多考虑合作制,而不是全盘集体化。可惜那时候一边倒学苏联,初级社还不过瘾,非向高级社——集体制是也——过渡不可。还不过瘾,大办人民公社,在一个更大范围内以不断增加的人口细分土地。
湄潭提醒我们,以承认集体经济为前提的家庭联产制,尚不足以扭转上述逻辑。喊稳定也没有用,因为内生一个不稳定。改革还要加一条,农户之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才彻底告别与中国传统和中国国情脱节的苏联特色的集体经济。
-
IPO财务核查效力有多大 堰塞湖仍有压力 高顿教育 2023-06-07 10:0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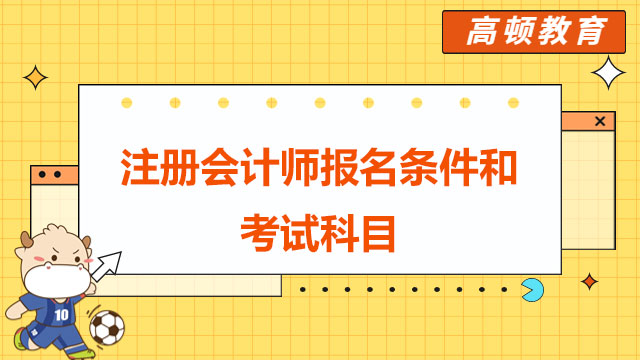
-
CPA考试可以自学吗?怎么学? 高顿教育 2022-05-29 09:06:25

-
2022年的税务师教材什么时候可以购买 高顿教育 2022-01-26 09:24:41
-
大数据应用促税务稽查提质增效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7:03
-
国家税务局: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超万亿元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