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段时间美国学者傅高义的着作《邓小平时代》受到广泛的阅读与讨论,借此由头,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得失也又一次得到了大家讨论。但在我看来,这几十年的改革历程无非是把一个计划经济体改变为了重商主义的经济体。所谓的重商主义思维盛行于15至18世纪的欧洲,那是早期资本主义兴盛时期,但这个词多为后世的学者所使用,在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时代,大部分人其实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重商主义国家大多是较晚向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国家,它们没能赶上殖民者直接抢夺黄金白银的热潮,因此它们没有足够的黄金白银用以货币发行,经济因而受通货紧缩的困扰。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换了一个经济思路,那就是鼓励出口,换回贵金属,就可以扩大货币发行的基础,这对于GDP的增长有直接促进的作用。用今天的语言概括,重商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外贸主义。它主张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尤其是要垄断对外贸易,以各种经济干预手段来追求国际收支的盈余,从而为国家积累财富。换个说法,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可以说就是今天的“中国模式”。
但这个模式是存在着诸多问题的。早在17世纪,就有英国人批驳重商主义学说,认为政府干预外贸实际上并不能为普通人带来财富,而仅仅是为政府增加收入。这无疑是不公平的。而只有更宽松的经济政策,才会真正使生活在国家中的每个人受益。但这样的批评在当时绝对不算是主流。15世纪以来的主流经济思想被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托马斯?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左右着。他们的基本信条是,只要能够实现外贸盈余,为国家积累货币财富,那么国家完全有理由直接干预经济、进行财富“抢夺”。而国家干预经济的体现之一,便是像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南海公司等持有政府“特许状”的国有公司。
重商主义的显着特点除了唯外贸论、政府干预经济等等之外,便是产生了“政企不分”的国有股份公司。这些与政府联系紧密的公司获得经营权的方法是凭借皇家颁发的特许状,特许状赋予它们在某一商业领域的专营权(patent)。英文“patent”一词如今指“专利权”,多适用于发明创新方面。但以起源而论,它的意思却是指得到政府认可的独断经营权力。透过这些手执政府批文的企业,政府实际上成为了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历史上最早的国企,就在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里产生了。
但是,当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时,应该由谁来对它进行监管呢?答案是,没有人。监管本来就是政府自身的职责,而已经直接参与经济的政府不可能会自己监管自己,就像在球赛中一个人不可能既是球员又是裁判。这种角色的错位,打乱了游戏规则,也使得政府与企业有了在资本市场狼狈为奸、违规操作的可能性,同时,获得政府所授予特权的国企进入市场,必然会利用政治特权对民众的财富进行“抢夺”,这显然不利于民间经济的健康发展。
随着18世纪末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市场理念在欧洲确立,重商主义学说逐渐变得不再流行。在今天的不少人眼里,重商主义仅仅意味着一个历史概念。但实际上,重商主义的思维并没有真正消失,在当代,它依然存在着,其表现为两方面:对外,新重商主义政府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对内,政府的权力大肆扩张,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谈到20世纪后半叶秘鲁的经济受到重商主义传统的影响时,就曾总结说:政府的唯意志论,是重商主义理论在今天的典型特征。它宣称,“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是政府主观行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重商主义思维与数百年前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再举一个身边的例子。台湾经济史学家赖建诚在《重商主义的窘境》一书里也谈到台湾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商主义”思维。并且,赖建诚认为,虽然现代的重商主义思维在台湾多表现为外贸上的“金块主义”,但就普遍情况而言,重商主义通常是和国家主义并行的,而国家主义则会产生管制经济与垄断利润的追逐。在管制与垄断的情况下,财富的最终流向不可能是普罗大众。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重商主义四个字都与政府扩张的权力、垄断经营以及对自由经济的干预等等情况有割不断的联系。一个受重商主义思维影响的强势政府,不可能在经济活动中考虑“公平”与“合理”这些概念,而在重商主义国家的市场中,随处可见政府代理人的身影。他们像普通的经营者和投资者一样进行着商业活动,但却或明或暗地体现着政府的意志;他们表面上有着*4的经营业绩,但实际上整天思考的却是如何打通层层权力关系;他们有时也会受到政府的惩罚,但更多时候获得的却是庇护;他们自私而贪婪,但这些人的私利却被畸形的市场纽带与国家利益绑在了一起。
如果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重商主义式的经济体,那么这样的改革无疑是不完善的。当然,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不会遵从于改革者的设计,而是自有规律。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的过程也是自上而下的民权运动和劳工运动兴起的过程。当“社会”和“民间”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时,依靠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便难以为继了。但如果“大政府”的模式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就无法走出重商主义,说直白点,在这种情况下,钱的大头还是让最有势力的生意人——政府赚走了。
-
IPO财务核查效力有多大 堰塞湖仍有压力 高顿教育 2023-06-07 10:0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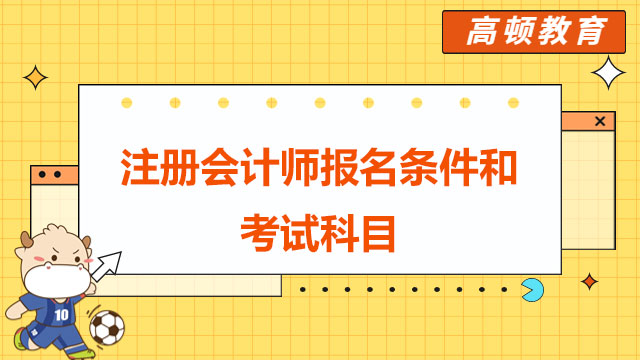
-
CPA考试可以自学吗?怎么学? 高顿教育 2022-05-29 09:06:25

-
2022年的税务师教材什么时候可以购买 高顿教育 2022-01-26 09:24:41
-
大数据应用促税务稽查提质增效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7:03
-
国家税务局: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超万亿元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