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G20集团及多个智库机构召开的会议都表明,全球各方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由通缩压力和金融不稳定性增强所导致的全球经济风险。而中国为减轻这些风险所选择的路径至关重要。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只是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建议采用西方常规的浮动汇率制度,将其作为应对变化莫测的资本流动的减震机制,并为货币政策松绑以便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流动性,但决策层却并未采纳放开汇率的政策。这让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和全球金融市场如释重负。
许多人原本担心中国会用汇率贬值来摆脱通缩,而其后果必然是全球范围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以及进一步全球通缩。但中国意识到如果坐视世界经济深陷资产负债表衰退状态,那么因国际贸易形势持续疲软而导致的全球总需求缺乏,就将进一步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
当然,中国仍然需要找到应对资本外流的手段,同时推动一系列能让其经济走上可持续长期增长道路的结构性改革。正如我们最近撰文指出的那样,关键是保持大约6.5%的经济年均增速,这就需要实施一系列旨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多层面短期稳定经济计划,以抵消重组低效率产业和消除产能过剩所带来的短期增长及收入损失。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将承担着既要保持汇率稳定又要打击通缩的艰难重任,包括确保能以合理的利率,提供中国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和消费驱动转型所需的流动性。考虑到中国为刺激经济和稳定汇率所动用的官方外汇储备金额,以及去年资本外流的规模——相当于去年全年经常账户盈余的三倍——稳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类宽松策略将是关键。
当然,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相应地适当收紧外汇管制。它也在考虑是否需要其它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比如某种托宾税(在1972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首次提出的金融交易税)以遏制资本的急剧跨境流动。
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可以归纳为振兴全球经济的“A方案”,它们是为防止中国陷入通缩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策略。但在当今多极化的全球体系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枪匹马让全球经济免于债务通缩。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还必须考虑实施一项更积极的共同战略,也就是振兴全球经济的集体行动“B方案”。
当然,集体行动并不容易。比如,构建并实行一个全球一致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就被世界各国[*{b}*]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排除,而那个会议上订立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我们现在还在用。当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稳定威胁之时,或许是时候再召开一次布雷顿森林那样的会议,以确定哪些集体行动措施是现在有可能实施的。
环顾全球,好像有足够的激励因素促使我们行动起来。随着发达经济体面临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庞大的公共债务负担、捉襟见肘的货币政策,以及难以驾驭的党派政治,全球经济摆脱目前通缩道路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经济体。虽然这些经济体也都各自面临着挑战,但它们的人口结构更为合理,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并拥有极大的生产力增长潜力。这些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可以激活庞大的需求并强化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通过在当地建设旨在减少全球资源消耗和应对全球变暖的可持续基础设施。
令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无法发挥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是资金短缺,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各类国际机构却无能力施以援手。如果世界要摆脱债务通缩陷阱的话——更不用说要解决不断恶化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这种窘况就必须有所改变。
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在庞大而急剧的跨境资本流动下保持稳定,甚至那些以巨额外汇储备的形式为自己买了保险的国家也不例外。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在2007-2009年间摆脱流动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美联储愿意与各大发达国家(多为美国盟友)的中央银行进行流动性货币互换。只有建立一个全球流动性货币互换保险体系,以多边货币互换安排为基础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各国才能实施全球一致性通货再膨胀政策,而免于对资本外逃和汇率贬值的过度恐惧与担忧。
最后,我们需要集体行动来使目前各主要大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变得更有效。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都未能重振全球经济的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和其他贷款人都将从央行获得的流动性留在了金融体系内,而没有投资于中小型企业贷款、长期基础设施,及其他实体经济项目中。
这不是巧合,2010-2014年间,全球*5的银行、企业和投资基金手中持有的现金增加了3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同期各储备货币发行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规模。我们今天亟需通过全球集体行动使各国消除产能过剩,降低杠杆率,并平衡税收政策,同时降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些有助于摆脱通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集体行动,将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厌恶情绪,从而提高各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效率。
达成全球共识一直以来都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在今天的背景下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各国继续这样单打独斗下去的话,整个世界都将因此陷于苦难之中。
本文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热门资讯
-
IPO财务核查效力有多大 堰塞湖仍有压力 高顿教育 2023-06-07 10:0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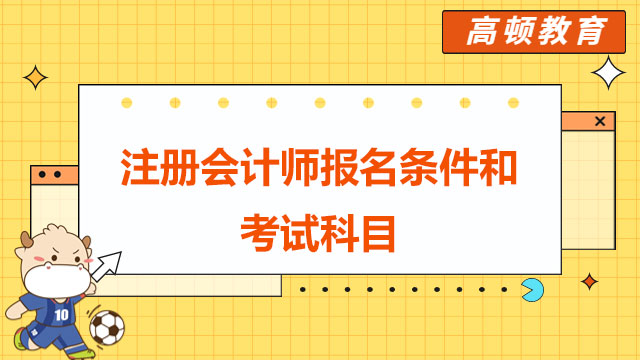
-
CPA考试可以自学吗?怎么学? 高顿教育 2022-05-29 09:06:25

-
2022年的税务师教材什么时候可以购买 高顿教育 2022-01-26 09:24:41
-
大数据应用促税务稽查提质增效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7:03
-
国家税务局: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超万亿元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4:50

热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