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正在浏览“业界评论”频道的网友吗?高顿网校小编邀您来阅读这篇11月24日的文章:罗惠良分析称突破发展瓶颈货币调控渴求未来新思维模式
未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将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与其相适应,货币调控需要跳出固有约束,依托新引擎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持续不断地突出全局性新框架。尤其需要提升并巩固央行的独立性,降低对货币政策调结构的期望,从更高层面协调推进整体改革的政策组合。针对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需求错位,依托新型金融机构构建完善的多层次普惠金融系统,尽快推动金融服务功能复位,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不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未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将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与其相适应,货币调控需要跳出固有约束,依托新引擎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持续不断地突出全局性新框架。尤其需要提升并巩固央行的独立性,降低对货币政策调结构的期望,从更高层面协调推进整体改革的政策组合。针对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需求错位,依托新型金融机构构建完善的多层次普惠金融系统,尽快推动金融服务功能复位,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不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年初以来,央行渐次利用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9、10两个月通过中期借贷便利(MLF)的结构性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定向注入了7695亿元流动性,但调控效果远不如预期。看央行*7数据,10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483亿,大大低于市场预估;当月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少增2000多亿,1至10月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减少4613亿。
据笔者观察分析,未能如期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的流动性,大致去向有三。一是资本外流。10月,银行结售汇逆差和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规模分别达1673亿和1462亿,均创历史新高。中国金融市场的资本外流和对外实业投资的转移资金相并存,境内资金存量总体减少。二是脱实就虚。据测算,目前累计已有76家银行发行了总规模达1.41万亿的同业存单,而6月末这一数字仅为1406亿。观察三家获得MLF的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其主要生息资产配置均为债权性证券投资。足见,金融系统内的“货币空转”仍有增无减。三是库存及占用增加。如按M2增速与GDP增速之间的数学关系判断,12%至13%的M2增速足以满足不足8%的经济增长所需。但我国货币乘数却在4.2-4.3倍左右徘徊,与危机前的4.5-5.1倍相比还有不小的回升空间,企业占用资金依然高企。
这样的结果,与我国金融系统设计、相关制度安排及宏观经济基本面均有关联:正规金融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结构性缺口引致金融服务覆盖不够,在实体经济薄弱领域融资缺乏针对性配套制度,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与资本存量的回报率呈不断现下降趋势,资本存量与产值的比值逐年递减,投资边际收益率逐年下降。
造成实体经济某些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系统及银行结构不合理、金融资源供给与企业需求间存在错位,本应由资本市场承担的融资功能转由银行体系承担。统计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数量占比仅1%,企业类型分布呈“金字塔形”,而金融资源65%由国有控股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掌控,呈“倒金字塔形”。现有非专营性金融组织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对实体经济的分散性资金需求缺乏支持动力,尤其在政策紧缩期更将其排挤于正规金融之外。据测算,我国银行对规模或限额以下企业的贷款覆盖率不及5%。
由于中介信息服务体系不健全、多层次担保体系缺失加剧了银企信息不对称和弱势行业与企业的融资难,而国家政策针对企业类型的划分标准不完全一致、差异化政策可操作性不强,也使得融资政策难以在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稳妥落实,为规避“融资搭便车”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资金支持行为谨慎,无形中增加实体经济薄弱领域的“融资难”和“高成本”。
据世界银行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已从1978年至1994年期间的46.9%,大幅降到2005年至2009年期间的31.8%,目前正进一步降至28%。相比之下,投资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显著提升,对应时期的贡献度分别为45.3%、64.7%和65.9%。进入后危机时代,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路径不明的产能转移、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严重地制约着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银行风险偏好中枢下移,无风险收益的生息资产配置成为商业银行的次优选择。
依笔者之见,建立新的调控模式,不断提升货币调控效力是突破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治本之策。首先,依托新引擎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处于增长动力转换期,过剩产能转移路径尚不明晰,新的增长点未能及时形成,找到[*{c}*]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成为释放有效需求的前提。在人口红利消失,或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增加资本投入时,要求机器设备本身包含技术进步,以及操作者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对各类人才、科技、工艺创新的要求加大。促进科技进步、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是确保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另外,“一带一路”规划的落地实施必将带来未来十年最为重大的政策红利,经初步测算,未来5到6年仅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就高达8万亿美元,抢抓并握牢重大政策红利,是当前加快增长动力转换的重中之重。
其次,要提升并巩固央行的独立性,降低对货币政策调结构的期望,从更高层面协调推进整体改革的政策组合。周小川行长稍早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明确表示“央行把改革发展也作为重要目标”。但现实的突出问题,恰恰就在于“三农”、小微、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甚至有些完全属于公共服务性质的领域,仍过于依赖银行贷款,而财政、债券等应有职能长期缺位。因此,厘清央行政策目标与整体改革关系任务很艰巨。可参考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谱系,综合运用常态化、结构化工具,坚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主基调;加强与银监会、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政策协调。
再次,针对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需求错位,依托新型金融机构构建完善的多层次普惠金融系统,尽快推动金融服务功能复位。加快新型金融机构建设,构建层次分明的普惠金融系统;消除民间资本进入壁垒;建立完善的新型金融机构资金补充机制;从政策上鼓励新型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信贷管理方式,推动其拓宽业务种类和服务范围;细化银行差别化监管政策,除现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外,在资本充足比率、拨备覆盖率等监管指标和公司治理要求上,对新型金融机构实行独立标准,适度提高其贷款风险容忍度,实行差别化监管政策。
最后,我国直接融资比例仍偏低,未来要以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继续完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场外市场,不断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舒缓间接融资依赖,扭转融资结构失衡格局,为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提供匹配的融资选择;改变信贷市场、股市债市、信托市场、民间融资市场等融资渠道的分立格局,在统一均衡市场中合理安排融资结构,为企业提供“量体裁衣” 式的资金配置;以公司债券为突破口,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走出经济运行困局,使公司债券回归直接金融本位,实现由发行人(公司)直接向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发售,改变主要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从而使公司债券成为间接金融产品)的状况。
总之,未来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将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与其相适应,货币调控自然需要跳出固有约束,持续不断地突出全局性新框架。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经济师,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
来源:上海证券报
来源:上海证券报
热门资讯
-
IPO财务核查效力有多大 堰塞湖仍有压力 高顿教育 2023-06-07 10:0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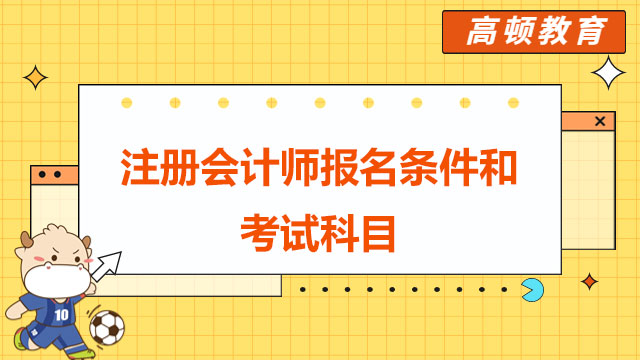
-
CPA考试可以自学吗?怎么学? 高顿教育 2022-05-29 09:06:25

-
2022年的税务师教材什么时候可以购买 高顿教育 2022-01-26 09:24:41
-
大数据应用促税务稽查提质增效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7:03
-
国家税务局: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超万亿元 高顿教育 2017-11-08 11:54:50

热门推荐



